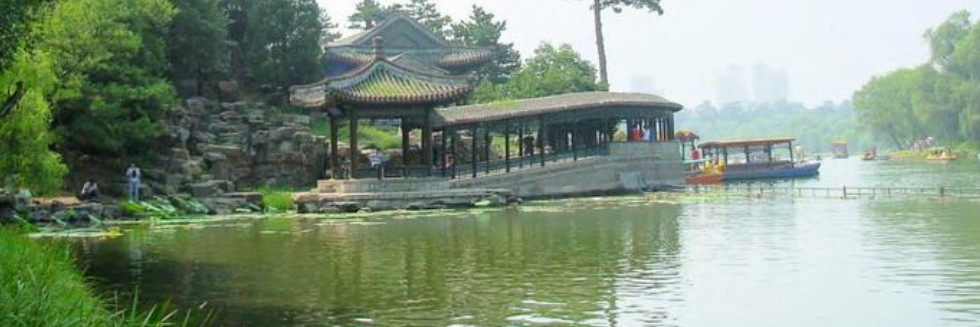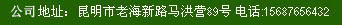|
文/观察者网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 “就是你的内心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比如我的内心,即使没有发这篇文章,即使大家不知道有韩春雨这个人,我的自我认同一直是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工作者。” ——韩春雨 年5月,中国最热的科技新闻人物是韩春雨博士,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5月2日,《自然生物技术》(NatureBiotechnology)在线发表了他的论文“DNA-guidedgenomeeditingusingtheNatronobacteriumgregoryiArgonaute”。我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化学,对生物学了解不多。不过根据我对这项成果有限的了解以及对科学规范的经验,可以试着大致描述一下这项工作的内容。此外,我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谈谈这件事对科学界、对社会公众、对青少年有什么启示,这想必是有更多人关心的。 韩春雨的成果究竟是什么? 韩春雨发现的,是一种以DNA为先导编辑基因的方法,简称NgAgo。此前最常用的基因编辑方法叫做CRISPR-Cas9,是以RNA为先导。CRISPR-Cas9技术是年发现的,然后它的应用出现了井喷,在三年之内创造出了巨量的成果。生物学家的评价是“很难想起曾经有哪一次科学革命像CRISPR这般如此迅速地改变生物学界”。作为一个例子,年中山大学黄军就副教授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工作就是用这项技术做的,他因此入选了《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学人物。CRISPR技术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许多生物学家认为CRISPR得诺贝尔奖是早晚的事。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韩春雨 年,有人发现了一种方法能以DNA为模板编辑DNA,叫做TtAgo。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需要在65-75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而大家都知道,人的体温是37摄氏度,大多数哺乳动物也差不多,所以使TtAgo的实用性大打折扣。韩春雨的工作,就是在TtAgo的基础思路上改进,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搜索和实验,找到了一种新的同源蛋白,能在37摄氏度下运作。 我对NgAgo的了解基本就是这些。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项重大的创造性成果。保守地说,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的可能性,给出了CRISPR之外的选择。至于它是否会取代CRISPR,是否会得诺贝尔奖,现在都言之过早。好比打开了一扇通往藏宝室的大门,里面的宝藏可能很丰富,也可能不太多。真正重要的不是现在就评估宝藏有多大,而是赶快去探索。 未来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最好的是NgAgo成为基因编辑的主流技术,获得诺贝尔奖。也可能跟CRISPR(以及将来可能发现的新技术)各有适用的范围,互相不能替代。还可能最后发现用处不大,大多数基因编辑还是要用CRISPR。这些可能性现在都不能否定,这是个开放的问题。但即使是最差的可能性,NgAgo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成果,必然会带动很多相关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许多媒体把它称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我的理解是,从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它是有潜力进入诺贝尔奖的考虑行列的,但如果以为一定能得奖或者得奖的可能性很大,那就过头了。 正如韩春雨自己的说法:“如果说此前的技术是一个菜市场,我们就是发现了另一个菜市场,丰富了人们的选择,而这个菜市场究竟好不好有待全世界的科学家去验证,当然我也会进一步探究。”(《副教授十年没发文章一夜变成“诺奖级”科学家》)别人都可以随意表态,而韩春雨本人谨慎是正常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的态度。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项研究不属于创新型研究,是跟风型的。这种说法其实有点见仁见智的意思。NgAgo的基本思路来自年的TtAgo,所以如果非要说它是跟风,也无不可。但是科研原本就是这样,任何成果都是有所本的。牛顿发明微积分是个神级成就,然而在他之前已经有费马、笛卡尔、帕斯卡、开普勒、伽利略等许多数学家做出了很多贡献。莫里斯·克莱因在《古今数学思想》中说:“微积分问题至少被17世纪十几个最大的数学家和几十个小一些的数学家探索过。”这其中还包括牛顿的导师伊萨克·巴罗(IsaacBarrow,—),他是剑桥大学第一任卢卡斯数学教授,发现牛顿的天才后主动把这个席位让给牛顿,堪称高风亮节的楷模。巴罗的《几何讲义》是对微积分的一个巨大贡献,简直可以说只差临门一脚了。难道我们要因此把牛顿称为跟风吗?所以我的看法是,任何科研成果都既有继承的因素也有创新的因素,只是两者比例的问题。这是个连续变化,没有截然的分界线。 中国的基础研究有了突破,仪器设备业就应该跟上。基于韩春雨的发现,可望发展出中国原创的基因编辑仪器设备,基因工程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自己原创基础技术,推动自己的产业升级,以至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像量子通信,这是最好的模式。 中国科技大爆炸,一场身边的革命 以上是对韩春雨成果科学意义的讨论。把这件事放到中国科技大发展的背景下看,会有更多的理解。 如我在《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中用许多硬指标说明的,中国科学家的重大成果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中国每年取得的基础研究成果仅以较大差距低于美国,跟英法德日处于同一层次,并正在显著地超越它们。 年就有好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大亚湾中微子项目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贻芳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被英国物理学会评为年度十大物理学突破之首,黄军就被《自然》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人物之一。 中国科技的爆炸式发展,社会大众可能了解还比较少,但对业内人士而言却是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事,已经习以为常,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道理其实很简单。杨振宁在年左右有个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谈到:“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这个道理看似质朴,却比很多大谈国民性、体制之类看似高深的观点都要深刻,因为它抓住了长期的基本面。 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证明了杨振宁的洞察力。美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是经济总量数一数二的繁荣国家,然而社会乱象丛生,黑社会横行,科技跟欧洲相比十分落后。用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AugustusRowland,—)的话说,“在科学方面,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版过或者即将出版任何中小学教材以上的书籍”。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美国的科学就迅猛上升,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占据了全球的制高点。简而言之,有钱有人有坚定意志就能搞好科技,这是个“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一般的真理。 年11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年科学报告:面向》。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28%,中国紧随其后(20%),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占世界人口67%的其他地区仅占全球研发投资的23%。此外,目前全球约有万科研人员,其中欧盟占比最多,达22%,其次是中国(19%)和美国(16.7%)。由此可见,中国对科研的投入已经达到了仅次于美国的高度,产出仅次于美国是理所当然的。 年8月,杨振宁在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20年内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将会获得诺贝尔奖。此论一出,遭到了许多名人经久不息的围攻(《屠呦呦获诺奖咱也不能忘逆耳之言说中国科学家得诺奖是做梦的言论都被他收集到一块了》)。典型论调如:“杨振宁先生是在说客气话。”“诺贝尔奖,并不相信杨振宁的预言。”“你见过奴才搞创新的吗?”“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过年也没戏。”“多年来,中国对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任何贡献。以后也不会。”……屠呦呦的诺贝尔奖揭晓后,这些人都成了小丑。 不过屠呦呦的成果是几十年前做出的,怀疑者仍然可以说现在不行,甚至认为现在不如以前。韩春雨的突破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就在当下,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就可以做出重大成果。这是最显著的一重意义。 年12月10日,屠呦呦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领奖现场。 迅速增加的板凳深度 韩春雨能引起如此广泛而持续的鍖椾含鐧界櫆椋庢不鐤楀摢閲屾渶濂?鍖椾含鐪嬬櫧鐧滈鍝棿鍖婚櫌姣旇緝濂?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河北省省级涉企收费
- 下一篇文章: 韩春雨事件即将结束,从另一视角回看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