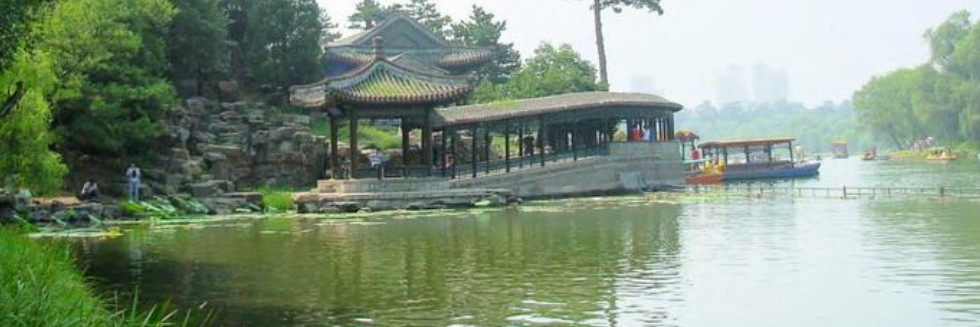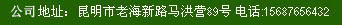|
本期人物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年生于上海,年到东北农场插队落户。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大学期间进入国家农委杜润生主导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参与农村改革的基层调研工作。大学毕业后,周其仁先后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发展研究所,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年底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曾出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题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作者 徐琳玲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成长轨迹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年代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5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所(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到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他对美国经济学界盛行的“黑板经济学”兴趣寥寥。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发展组成员之一、清史学者王高凌曾撰文回忆,年他随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车上感慨:“要是这时候(宋)国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 “这是他心里的几员爱将。”王高凌说。 发展所的学术协调人在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从年到6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一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王小强、周其仁去国务院印刷厂负责最后的校订。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时,周其仁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连党员都不是。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忆起当年开会讨论的场景,如今是昆百大董事长的何道峰笑出声来,“我后来和他开过玩笑,说他光做学术研究是可惜了,如果在别的地方,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鼓动家。” 在这一帮老同事们看来,除了研究能力突出,好口才也助了周其仁一臂之力。 当时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的蒋中一说,周其仁是最早提出了城乡不平等问题的人之一。“大概是3、4年,当时农村包产到户已经完成,大家在讨论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内部讨论得很热烈,观点很多。他们几个人就提出为什么农民的身份和市民不同,认为户籍制度把国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二步”,研究小组提出的另一项更重大的议题是:改革已存在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在被饥饿记忆缠绕着的共和国史上,粮食问题一直被视作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蒋中一说,当时许多中央部委包括农业部、商业部、计委的一些司局长们都有抵触,“情感上、政治上都有,非常坚定地认为粮食必须进行管制或半管制。但是,其仁他们问为什么非要政府管制?难道粮食这种东西没有商品属性么?” 周其仁后来回忆,他们那个小组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多功夫。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一起跟进的还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粮食研究小组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杜润生的肯定下,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双双派出秘书上山听会。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 回京后的一天,周其仁接到突然通知,让他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被中央警卫局的车子送上专列,他才知道中央领导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一开车,总理就召集开会,谈着谈着,他让“农口”来的小周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 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5年,统购统销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产销区两头“摆不平”。加之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粮价较大幅度上涨,市面上出现恐慌抢购,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干群冲突。中央内部和社会各方诘难四起,令杜润生和方案小组都受到了压力。 最终,中国的粮食市场化走了“很漫长、很艰难”的二十多年,终于终结了统购统销体制。 “能说的,不如会听的。”离开“农村改革的参谋总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听的人最难,他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选择,职位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多。而且,对这些约束条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听者会听,才下得了决心决策。” “当年,我们有幸接触的到那些很会听的领导人。” 回顾过往,戴小京说:现在当作一般常识来看的东西,在二三十年前是看不明白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路都有争议,“也许其仁那时候就预测到了。” 他和周其仁在6年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记录他们那时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否者“倒退也就难以制止”,一旦重建这种权利,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将需要全盘变革。 归国10年后,周其仁从年起又一头扎进老本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地调查研究,试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条变革现行土地制度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几乎每一幢新大楼下都埋着故事。”在中国近十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征地、拆迁而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市民之间的冲突、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 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我问周其仁:如何看待当年的“战友”、如今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此后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 “幸亏有个陈锡文!”他很干脆地回答。听者一脸愕然,他又补充:“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较‘中央’,不能冲到最前面。老话说守正出奇。中央守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胜当然好,逐步推进就是了。万一受挫,也无碍大局。因此,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时候,‘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当年农村改革都这么来着。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缝出一幅“真实世界”的图景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年,他一脚踏进江苏常州室公安局看守所。隔着铁窗,和铁本案的“主角”、民营企业家、刚刚入狱的戴国芳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一说起和周其仁调研的经历,自称外行的北大学者薛兆丰会频频使用一个词——“厉害”。 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他已经和接飞机的人聊上了,开始问问题了。途中,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个接着一个累得睡着了。耳朵里只听他的声音,他还在不断地聊,问问题,最后被他问的人也累得睡着了,他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的精力太旺盛了。原因之一是问题本身会激发他无穷的精力,他只会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人体美学欣赏赏世界著名的女人体油画集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